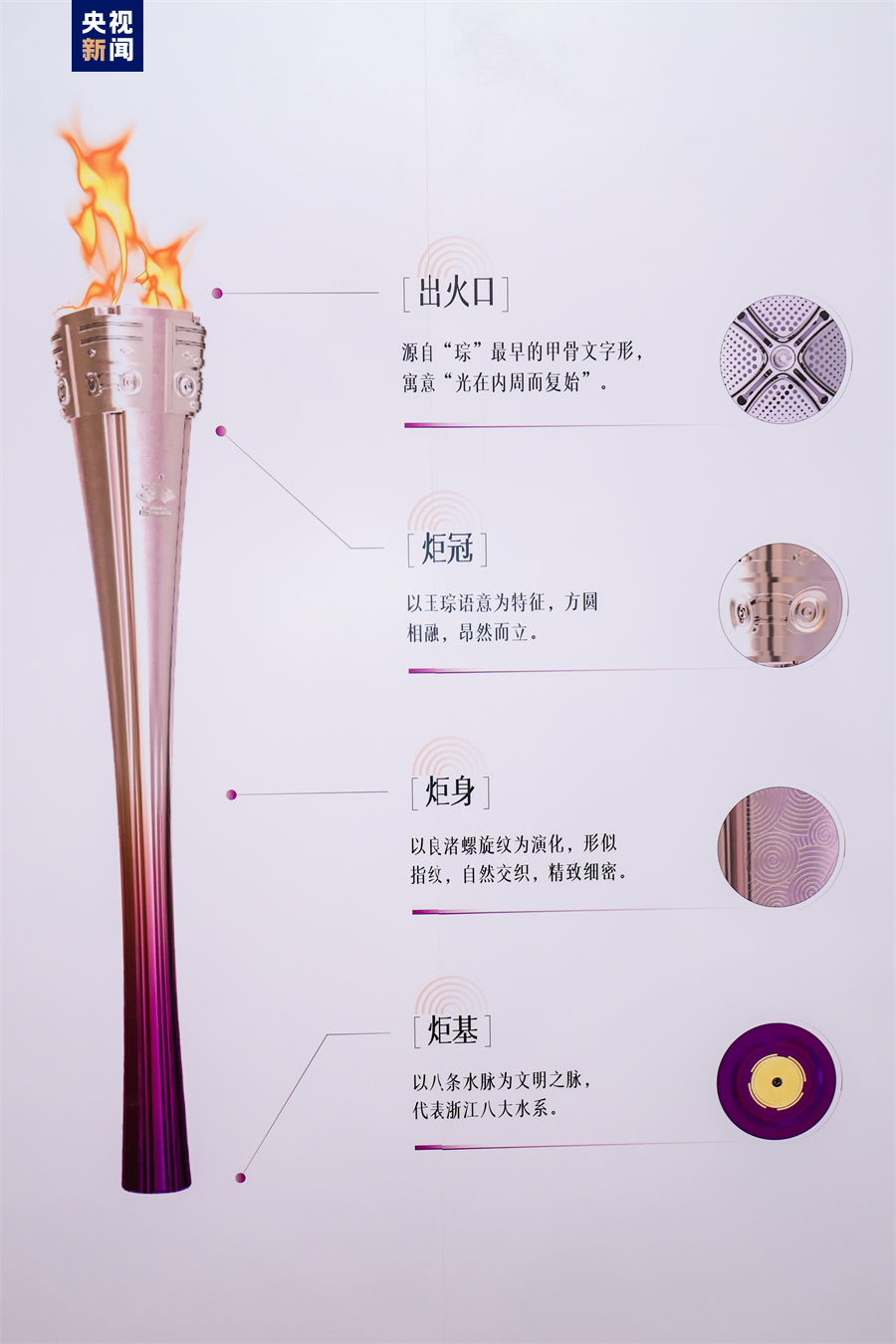怀念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啊—想念以前的日子的句子

文/李英俊
我的家乡很小很小,可是在中国地图上面的位置也还是能够找到。隔了多少岁月,流失了多少时光,提起那当年的旧事,还是历历在目。
皑皑白雪,白雪皑皑,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若不是因为过于寒冷,也许会令人生出些情真意切的遐想。
每年放寒假,父亲总是带着我到深山老林里去拉烧柴,记得那是最后一次。山路那么远, 十几岁的我耷拉着脑袋,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抱怨,不停地问父亲:“快到了吗?快到了吗?”父亲说:“快到了,快到了。”可是一走又是十来里还没有到。路上没有任何人,只有我们父女俩仿佛要把天底下的路走完。
终于到达了父亲心目中要去的地方,下了公路,我们又走了一段崎岖,没有蛛丝马迹更少人迹的山路,那是马套子曾经走过的路,我们把小拉车放到路边上,踏着没膝的积雪继续往深山里走,走到山坡底下,把那横三竖四埋在积雪里的朽木,一根根用脚驱出来,用弯把子锯锯成几米长的段,再从雪壳子里撬动出来,然后再一根根往外扛,扛起来还要走好几百米,甚至要扛好几里地。
父亲当然要扛粗大的我扛细小的,碰到更大的我和父亲一起往外抬,当然也是父亲抬大头我抬小头。我和父亲一前一后,深一脚浅一脚的压得我两腿发软,尽管趔趔趄趄的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走不稳,因此还被后面的父亲不停地数落着。
我们把一根根截好的烧柴弄到路边之后,太阳也到中午了,该下山了,于是坐在树墩子上开始休息。父亲点燃一支旱烟放在嘴里叭嗒叭嗒地狠吸几口,满足地吐一圈烟雾后,便站起来四处找一些干树枝子拢火。他把挂在腰间的大饼子解下来,那大饼子尽管拴在腰间,还是冻得硬邦邦的。等火苗子窜起来了,把大饼子用小木棒串起来在火上烤,烤化一层啃一层,一啃一遛沟,啃完了捧几捧雪吞下去就开始装车了。装完小拉车捆绑好了,还得打个摽,父亲拿着弯把子锯,看看哪棵小松树都舍不得锯,跑出老远锯了一棵小桦树回来,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满载而归了。
父亲站在小拉车中间驾辕,我把一根绳子拴在车辕右边,横挎在脊背上做他的副“驾驶 ”, 山路崎岖,沉重的小拉车在山路上七扭八拐,没走多远父亲就累得呼呼冒汗,我也喘着粗气呼呼冒汗,实在是太累了,可是父亲就是不说歇一会。等到下坡时一路颠簸,父亲收放自如地一路小跑,我也跟着一遛小跑就全当休息了。
我的两只棉手套,冻成了硬邦邦的两个冰坨子,手也硬邦邦的在里面佝偻着,自从那年开始,我的一双手一辈子都没有柔软过。 两只棉胶靰鞡也早就冻成冰疙瘩了,脚趾头冻得像猫咬,贼拉拉的疼,只得脱下鞋来用手搓一搓脚再穿上。生命中的水份在额头上一绺一绺的结成了冰溜子。父亲也一样,眉毛胡子不分主次的在帽子底下也结成了冰溜子。
上坡时父亲总觉得我不用力,用手不停地检验着我脊背上的绳套,唠叨着:“别把绳子磨断了,别把绳子磨断了。”听着这话我很生气,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太阳落山了,凛冽的寒风也不再那么刺骨。积雪覆盖着森林,月亮悬挂在黯淡的树梢上,陪伴着我们父女。离家不是很远了,我横挎着绳套,弯着腰,佝偻着脊背,撅着嘴,嘴一直是撅着的,我觉得自己是撅着嘴长大的,一干活我就和人家那不干活的女孩子比,觉得人家的孩子都是掌上明珠。一比就和父亲怄气。连母亲都说:“一干活你嘴上就能挂个油瓶子。” 路那么远,两腿发软实在是太累了,低着头反反复复地数着自己的脚步。一步,两步,一百步,五百步……。一步一步数着回家的距离。父亲说什么是什么我也不回,心里的那一股怨气,丝毫也不敢表现出来。可是父亲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像两只明亮的探灯,我想什么他都能看得出来。平时我那话匣子一样,口无遮拦的嘴巴,始终一声不语。
终于快到家了,东山坡一大段下坡路,父亲挺着胸脯用双脚控制着车速,我跟着又是一遛小跑。到家了,我急忙扔掉了绳套,扔掉了手套,踢开门跑到屋子里躺到炕上不说一句话。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上山拉烧柴,以后每年放寒假,我都一个人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上山。每年冬天总是重复着这种生活。
我家前院有一对双胞胎兄弟,我和他们一起上山。人家兄弟俩是两个十五六岁,正在青春期的少年,哥俩到山里捡柴火,就如探囊取物,轻而易举的放几棵老树干就够一小拉车了。我一个女孩子只能跟在他们后面,人家满载而归了,我也不得不跟着他们一起下山回家。有一次回家比较早,还没来得及卸车,父亲大人下班回来了,一看我车上的柴火,就带着轻蔑的口气对着母亲说:“看好了,别让老鹞子看见,老鹞子看见就给叼跑了。”母亲怼了一句:“嗯!她就是捡个金山回来,你也看不见。”
父亲的怨气也是冲着母亲来的,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孩子,我是老大。那个年代都重男轻女,父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四个女孩子只有我的名字是出生时,父亲找人认真起过的。我身下的几个妹妹,都按照出生的顺序叫了二丫头,三丫头,学名都是后院颇有见识的一个裹着小脚的田奶奶给起的。
父亲一双眼睛总是盯着老李家的双胞胎上,人家不仅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男孩,人家还有大儿子小儿子,父亲常说:“看看人家的孩子,各个都是杠杠的顶门杆。” 父亲担心李家没有续香火的,总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等到母亲生到第五个孩子时,父亲再也不用担心继承香火的问题了。在这之前若说父亲从来没有抱过任何一个女儿我不敢肯定,可我确定在记忆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后来对于两个儿子那种举在头上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的溺爱,连邻居都看得出来。
我最讨厌的是他那“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说教,在后来负责承载香火的两个弟弟身上,却一次都没有实施践行过。别说棍棒就连手指头都没有戳过一下。
勤劳也许是一种基因吧!不然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干活呢?他比所有的同一个时代的人干的活都多。父亲把强大的勤劳基因传承给了我,我在十四五岁时就学会了所有的劳动技能,劈材,挑水,凡是成年人能干的活我都能干。
尽管岁月艰难,尽管粗茶淡饭,靠吃土豆炖白菜为生,但是因为劳动身体还是逐渐强健起来,增加了体力。劳动是我的强项,邻居家的三妮子,秀梅,桂芝我们都一样。大家互相联系着,放寒假时可以结伴上山,尽管不放寒假,我们有时也起大早,天刚灰蒙蒙的,在十几度的寒流中到贮木场去捡木头头或者拉树皮,来替代好柴火。家里的柴火烧不完,每年都能卖几次,哪一年都能卖个七八十块,甚至百八十块,别小看这百八十块,在那个年代,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那时候买一斤玉米面才九分钱。
传承劳动是民族之魂,是智慧之源,让人受益终身的劳动如今被贬低了,把劳动者贬低成负面的座右铭。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孩子,没有循规蹈矩的上过学,可也不以劳动为耻。我也不例外,十六七岁的孩子习惯了这种以劳动为光荣的生活,哪怕顶着铺天盖地的大雪,哪怕顶着西伯利亚的寒流,也时常惦记着在上学之前,到储木场划拉一车树皮回家。
童年的我没有抱怨过苦难,没有抱怨过生活,我只是抱怨慈眉善目,一见人就笑容可掬的父亲,为什么就从来没有笑容可掬的夸奖过我呢?
图文:李英俊
编辑:海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