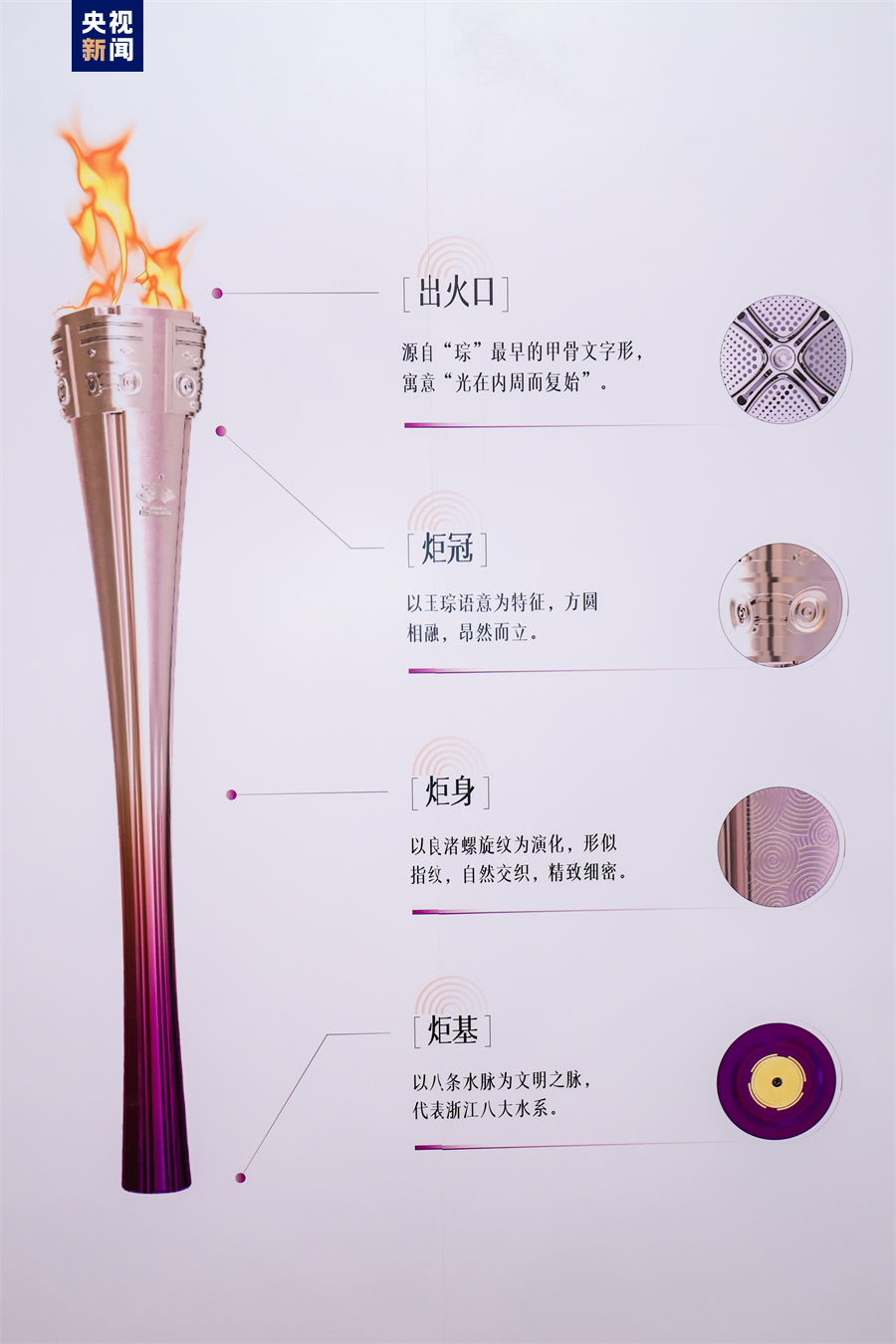诈骗五千已经退赃会开庭吗;诈骗4000元已经退赃罚金多少
作者:邓自华,来源:公众号“刑事法譚”。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非法集资案件总量居高不下,且呈现出公司化、集团化的犯罪特征,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职责清晰、分工明确,主从犯关系容易界定,且非法所得金额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另外,此类案件涉案金额往往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各被告人一旦被认定为犯罪,除会被判处人身刑之外,还会面临着对被害人损失的退赃退赔义务。近年来,司法实务中逐渐出现并日趋紧迫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包括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在内的牟利型共同犯罪案件,其中的从犯对于全案涉案金额是否均需承担连带退赃退赔责任?
对此,司法机关的传统做法是,根据“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基本理论,要求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对被害人因犯罪所遭受的损失连带承担退赃退赔义务。例如,在非法集资案件的办理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出台的《关于办理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第11条第二款规定:“参与非法集资犯罪的被告人(包括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业务员),应当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退赔责任,除应当依法追缴其获取的佣金、提成等违法所得外,还可以责令在其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范围内承担退赔责任。”根据传统刑法理论,上海市司法机关的上述规定及做法并无问题。
但近年来,这一传统做法所带来的弊端逐渐显现,地方司法机关开始寻求不同于此的其他路径,以在个案中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例如,同样是在在非法集资案件办理中,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第24条对退赃退赔范围的规定是:“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法所得与民事诉讼同被告对集资参与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所区别,追缴或者退赔违法所得不属于民事赔偿诉讼,不涉及民事连带责任的问题,应以行为人实际的违法所得为限,尚未追缴或者无法追缴的,可以依法责令退赔,退赔亦应以实际违法所得为限。”此外,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出台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7条中明确:“主犯原则上具有共同的退赔义务。首要分子按照犯罪集团所犯罪行的全部数额进行退赃和退赔,其他主犯按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数额进行退赃和退赔。从犯一般按实际违法所得进行退赃和退赔。”上述地方性司法文件对非法集资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从犯的退赃退赔义务范围作出了明确限缩,即以从犯实际非法所得为限。
这一问题值得关注,因在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案件中,对于从犯而言,其退赃退赔的义务范围甚至比其可能被判处的人身刑还要重要。我们认为,对从犯的退赃退赔义务范围进行适当限制是必要的。理由如下:
首先,不考虑从犯的非法所得,而要求从犯一律对涉案金额承担连带退赃退赔责任,不符合司法规定。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处置及被害人合法财产返还问题,规定在《刑法》第六十四条。在具体适用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其中明确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根据上述规定,对被告人适用“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前提是,被告人有“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情形。如果机械适用传统刑法理论,在确定从犯退赃退赔义务时,不考虑从犯实际非法所得的多少甚至有无,则对于没有任何违法所得的从犯(例如,在合同诈骗案中,犯罪所得全部归公司或者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相关从犯仅根据职责要求从事部分环节,未因其犯罪参与行为而额外获利),虽然其没有“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也要承担全部涉案金额的退赃退赔义务,该结论与上述规范性依据不符。
其次,不考虑从犯的非法所得,而要求从犯一律对涉案金额承担连带退赃退赔责任,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诚然,在给被害人造成损害的共同犯罪案件中,要求从犯一律对涉案金额承担连带退赃退赔责任,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因犯罪而遭受损害的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刑事司法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还需要兼顾各被告人所承担责任的均衡。在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电信网络诈骗、合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案件中,对于没有任何非法所得,或者仅有较少非法所得的从犯,要求其对涉案全部金额承担退赃退赔义务,则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可能导致,从犯实际被追缴、发还的财产,高于主犯,甚至会出现在整个共同犯罪案件中,“谁有钱谁吃亏”、“谁未转移财产谁吃亏”的不合理局面。虽然从理论上而言,从犯在履行超出自己应负责任部分的退赃退赔义务后,可以向其他共同犯罪人追偿,但上述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和落实,最终仍然可能导致从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倾家荡产”为主犯退赔,明显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普通公众的法感情。
最后,不考虑从犯的非法所得,而要求从犯一律对涉案金额承担连带退赃退赔责任,不利于被告人复归社会。因在相当一部分公司化运作的共同犯罪案件中,从犯的主观恶性较小、规范反对意识较弱,根据特别巨大的犯罪金额对其确定基准刑,并在该基准刑的基础上根据其所具有的从犯情节对此确定宣告刑,本身已经“罚当其罪”甚至“罚过其罪”,如再通过判决确定该等从犯与主犯负有数额特别巨大的连带退赔责任,则对于绝大部分行为人而言,无异于宣告其经济上的“无期徒刑”。例如,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对一名最为基层的业务员判处刑罚的同时,要求其对其涉案的5000万元集资额负连带退赔责任,对该业务员而言,穷其一生可能都无法清偿上述债务,由此导致,即使在人身刑和罚金刑执行完毕之后,该被告人及其家庭仍然承担巨大且毫无希望的经济压力,无法真正地复归社会,反而可能由此使被告人及其家庭成员滋生反社会心理。因此,不考虑从犯的非法所得,而要求从犯一律对涉案金额承担连带退赃退赔责任,也不符合刑事司法的教育改造导向。
因此,我们认为,在牟利型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害,各被告人之间的退赃退赔义务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对于其中的从犯,应以其非法所得为限确定其退赃退赔义务,对没有非法所得的从犯,不应要求其退赃退赔。对于其中的主犯,也有必要进一步予以区分,例如,对于在公司化、集团化运作的共同犯罪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对涉案全部金额承担退赃退赔义务,自无异议。但对于上述人员之外的其他人,虽在共同犯罪中起相对主要作用,但并不实际控制资金流向、用途和分配权限,实际非法所得相对较少的,其退赃退赔义务范围,可交由司法机关根据该被告人的作用地位、退赃退赔能力及其他共同犯罪人退赃退赔情况等因素进行自由裁量。
同时,我们看到,在有明确地方性司法文件之外的范围,部分司法机关也在尝试探索对从犯的退赃退赔义务予以限制。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01刑初69号、(2020)京01刑初9号刑事判决中,在认定各被告人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基础之上,对于没有实际非法所得的从犯,并未确定退赃退赔义务,而仅责令主犯予以退赃退赔。上述判决,足以作为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蓝本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