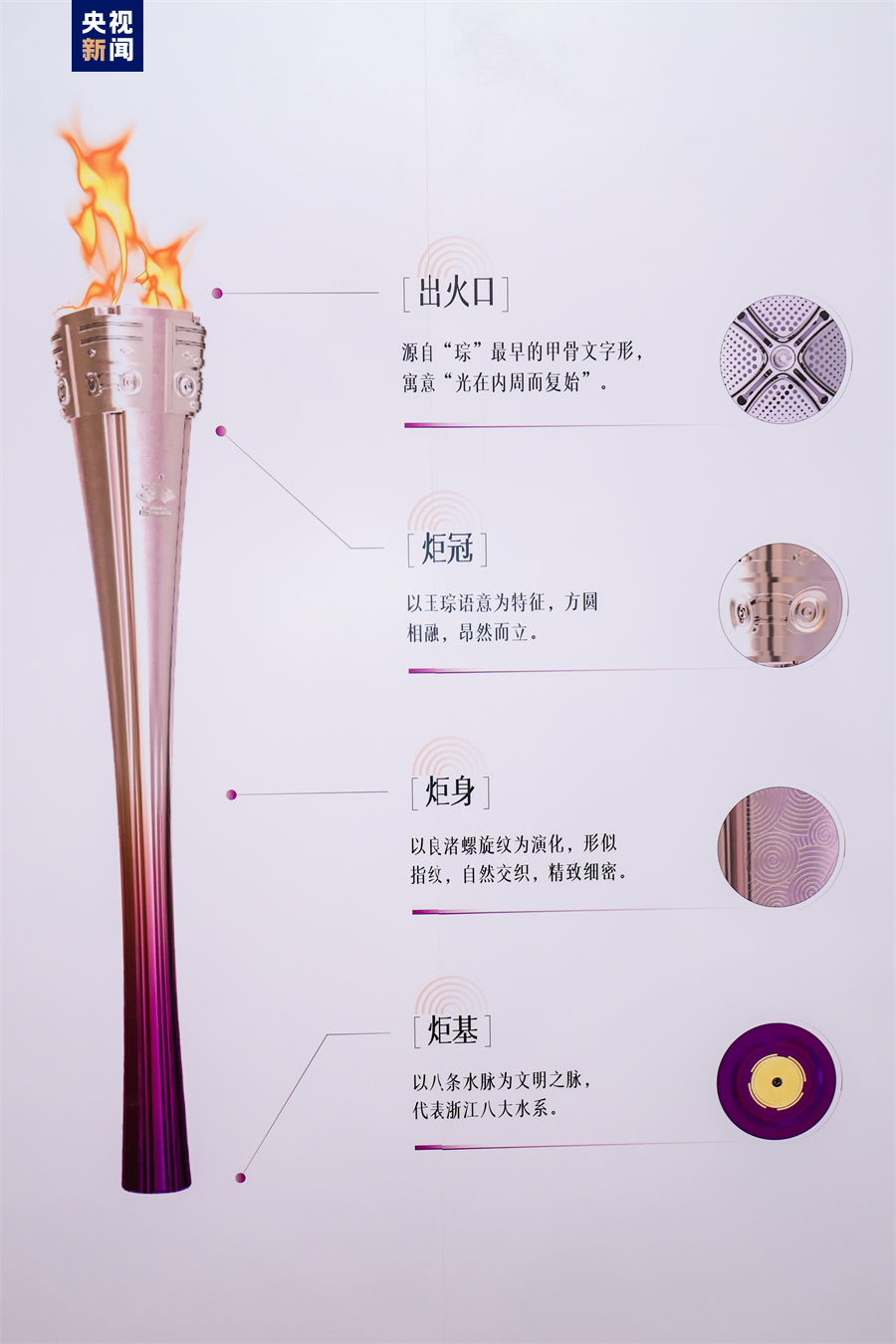无边落木萧萧下的下一句,不脱蓑衣卧月明的上一句
作者 | 瞿长海
校对 | Sakura286
杜甫一生,有不少出色的绝句流传后世,诸如“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都是匠心独运、妙手天成。然杜甫平生心血功力,大半在律诗;其律诗中佳作,多为七律;其七律之魁首,则为《登高》。换言之,读懂了《登高》,便攀上了一座唐诗的高峰,对话了一个伟大的心灵。

律诗,萌芽于南朝齐永明时沈约等人的新体诗,初时对仗单调、音律不齐,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隋代的杨素、卢思道,用南朝靡丽词彩给他做襁褓,用北地清新刚健之气给他做衣裳。初唐四杰教他站立行走,宋之问、沈佺期教他开口说话。盛唐的王维、李白、高适、岑参反复锤炼他,令他身强体壮、百病不侵。
至此,律诗的成长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他能走路,会说话,身体健康茁壮,能与人流畅交流,偶尔还能说出“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样的佳句。
但是大家还是不愿意跟他玩。作为一个孩子,他似乎还少些了什么,那东西并不大,却十分重要。缺了那东西,他只能一直在文学殿堂的二门处徘徊,不能登上三宝。
他一直徘徊到公元767年,看见一位老人自浣花草堂蹒跚而来。老人破衣烂衫,又咳又喘,脸上满是疲惫,眼睛里却有红热的火炭。见了律诗,老人突然怔住了,激动得双手颤抖。沉吟良久,他提起笔来,在这孩子的双目上点了两点。于是律诗睁开了眼,两道神光照穿苍穹,神采和灵气在他身上勃然挥发。
律诗有幸遇上了杜甫,得以登堂入室,成为唐诗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而杜甫亦有幸遇上了律诗,他戴着这颗明珠坐稳了“诗圣”的宝座。而公元767年,那载入史册的点睛之笔,就是这首《登高》。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公元765年5月,杜甫最后一次离开浣花草堂,这年他53岁。他身体很差,头发雪白,身染肺炎,手脚风痹,已经实在不是适合出游的状态。但他没有办法。一个月前,好友严武去世,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只能另去投奔。
然而“访旧半为鬼”,知交大多零落,他一路来到夔州,并无一人愿意接济,只得在夔州暂时定居。在这里,他置办了一间草屋,养了一些鸡,租了一些田让家人种。
随后,蜀中战乱,士兵造反,吐谷浑、吐蕃等外族不断入侵,官军没能力剿匪,杀起百姓来却是一把好手。“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乱离之人,不及太平之犬。杜甫默默看着。不知他有没有记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豪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语。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梦醒之时,不见了大庇天下寒士的茅屋,天宝旧事如月落时分呜呜绕梁的一曲长笛——罢了,罢了。杜甫长叹。自己这个样子,又能做得了什么?“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于是,诗圣真的老老实实养起了鸡,与彝族人打打交道,在病榻上研究研究格律,提着拐杖四处散散心。但越散心,他的心里越发郁结。他听到吐蕃又攻占了甘州、肃州,各地军阀日益跋扈,蜀地的大乱刚平定,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又造反。百姓的哀哭还在耳畔,朝廷的急报如同骤雨,杜甫的心焦急得如同炽热的火炉。
听着江声,他彻夜无眠,胸中的块垒无法平息。公元767年秋,他终于按捺不住,拄着拐杖,登上了夔州的一座小山。眺望长江,他的心里感慨万千。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开篇就对仗。似乎有些急不可耐,什么东西满满郁结在胸口里要往外冲。登高眺望第一眼,看到的这副景象,读者们有什么感觉?就是“动”。站在高处,看到的一切景物都更渺小了,风吹草动应该更不易察觉才对。
但在杜甫眼里,高天下风在急速回旋,猿猴声声长鸣属引凄厉,长江浪涛拍击着沙岸,无依的白鸟在半空中反复盘旋哀鸣。这是一副多么动荡、多么悲凉、多么不安的景象啊!
古人都爱登高,所见则不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是壮志者看到的,“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是失意者看到的。而“风急天高猿啸哀”这类的景象,只存在于乱离人的心里。风动,幡动,心在动。心系家国,所以站得再高,依然能看见乱离的白鸟、哀鸣的猿猴,听见天下横流的沧海。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杜甫历来被视为现实主义诗人,但在这一刻他却饱蘸了屈子的血、楚辞的魂,一字一顿,力有千钧。秋为刑官,又为兵象。历史有兴乱更替,四季有春生秋杀。天下大乱、干戈四起之时,正是秋之余烈摧败零落之日。而今吐蕃侵犯,官军残民,“野哭千家闻战伐”,秋意也在这一年肃杀到了极致,诗人握笔的手也被这秋气吹冷、吹疼。他写道:“无边落木萧萧下”。
而滚滚流淌的长江,亦是隆隆前进的历史车轮,是逝者如斯的时间长河,是冷酷无情的造物主永不停息的节奏:历史总要向前,时间总要流逝,一千个一万个诗人登临凭吊,长江也自滚滚而来,不会快半拍,也不会慢半拍。
人的渺小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人的无奈与悲哀不着一字而全出,更兼对仗工整、音律铿锵,若要找全诗之眼,是这两句;若要找杜工部集之极意,是这两句;乃至要找沉郁顿挫风格之典范,亦是这两句:好一个“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人终于将笔落回到自己身上。他在首颔两联,见的是天地众生,颈联回到自己身上时,依然气势不减。他依然有这个底气,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他同样做到了时空的极致。
时间上有“一百年”,是他的贫病交加,多少次他独自登高,念天地之悠悠;空间上有一万里,是他的半生漂泊,偌大的华夏他不曾有一个故乡。然而一百年,一万里,到底图的是什么呢?这是哲学里无解的叩问。
此时杜甫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而他反思自己的一生,并未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于是他颓丧了,在尾联只发出了一声长叹:“历尽了艰难苦恨,白发长满了我的双鬓;我衰颓满心,只能暂停了浇愁的酒杯。”前六句“飞扬震动”,到此处只“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
这首惊天动地的七律,到这里就结尾了。杜甫在给那个孩子点上眼睛时,不知有没有想过,当自己的生命早已终结、大唐也成了古书上的吉光片羽之后,那个孩子依然纵横于世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感染着千百年后的一代又一代读者。
在杜甫活着的有限年岁里,从没有人认识到他是个怎样的天才,所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然而历史并没有埋没任何一个有才者。千百年后,人们终于给出了公正的论断:《登高》,千古。杜工部,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