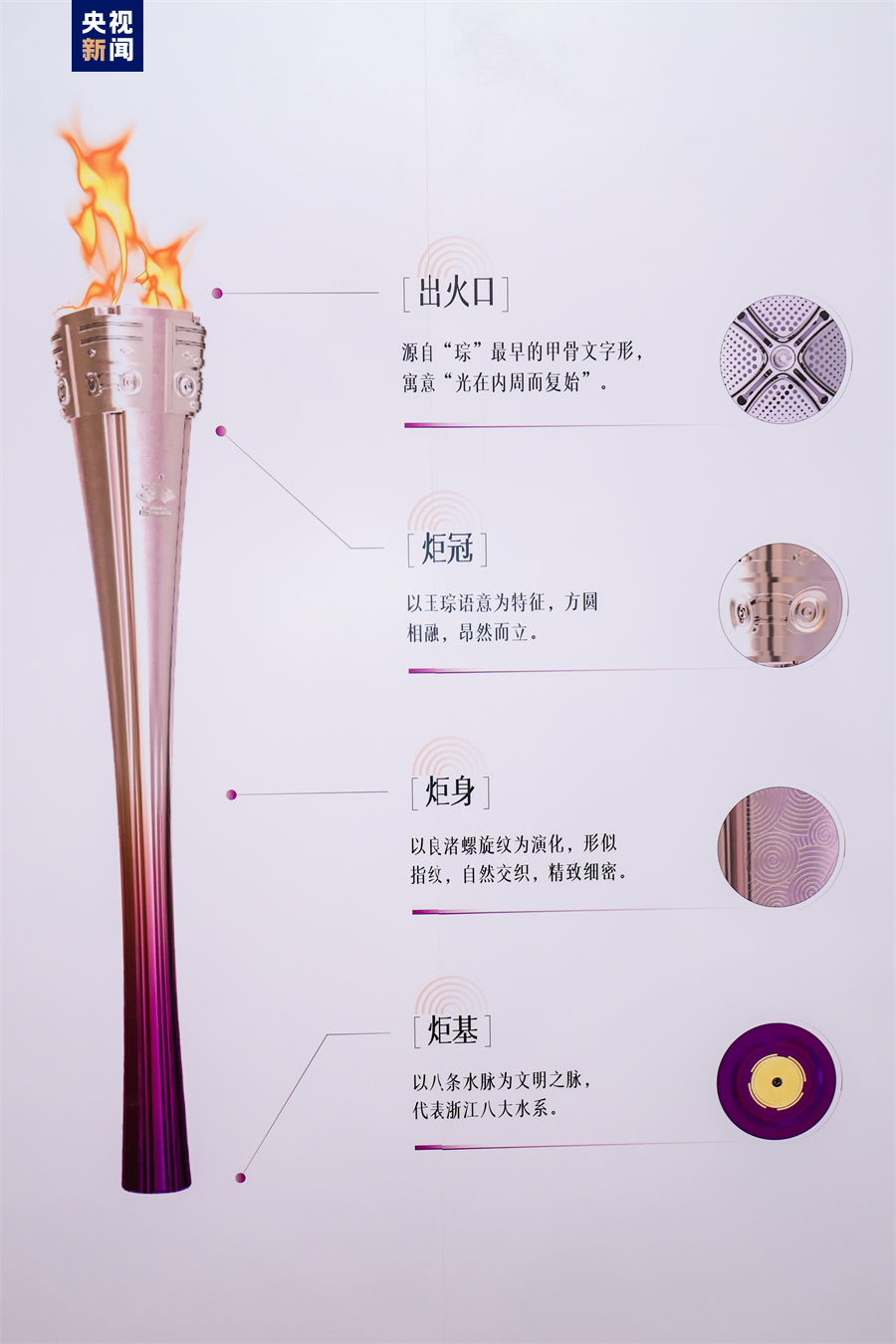类似和月折梨花的古言、类似和月折梨花这类小说

那婢女闻声顿足,投向沈姮的目光里携着疑惑。
饶是沈姮素来好性情,在伯府也从未刁难过下人,此时为达目的却不得不拿出一副严厉态度来,冷着张脸诘责道:“难怪我刚刚经过王爷寝堂前,见地上洒了一路的香灰,原来是你个粗心丫头弄的!”
二人虽同为王府下人,但那婢女见沈姮的裙衫比自己高一等,自不敢顶嘴。回头看了眼来时路,果然洒着零星的香灰,再检查手里提盒,便发现问题发在。
“多谢姐姐提醒,我这就清理干净!”说着回身要找扫帚。
“等等,”深姮将她唤住,语气和缓下来,透着好心提点之意:“这里急什么,先去将王爷门前处理干净吧,免得受责罚。”
小婢女目带感激的颔首谢过,匆匆去了。沈姮则赶忙悄悄尾随上她。
这一路廊腰缦回,甬道纵横,若非有她作引路人,沈姮断是难找过来的。最后那婢女停在一处朱柱粉壁奇伟华美的小殿前,开始低头在地上仔细找寻。
沈姮知道,这便是宸南王的寝堂了。
来此之前她已预料到堂堂宸南王的府邸必会奢侈宏丽,可如今站在这座小殿前,近在咫尺的见证着,她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没进过皇宫,不知道皇帝住的太极宫长什么样,但若有人告诉她这里就是太极宫,她定是深信不疑的。
被她诓来的那个小婢女焦急的沿着一条道找寻,渐渐远离了门前,沈姮便即闪身进去。
此殿面阔五间,进深九架,除却宽敞外雕饰亦是极为华美!就如头顶的棋盘格平闇以金笔细勾,仰头看去犹如一匹烂漫织锦。殿内的其它陈设同样精致,单独取出每一件来都可道出不凡来历。
本以为殿内并无人在,沈姮游逛间突然听见有瓶瓶罐罐轻轻挪动的声响,不由将心一提!
循声往东瞧去,一扇十二牒的云母长屏遮住了视线,其上隐隐有两道纤细的人影晃动。看来是有婢女在里头洒扫,所幸她刚刚脚步极轻并未引起她们的注意。
虽说眼下自己也扮作了府里婢女,可言多必失的道理她亦晓得,不与她们接触才是最稳妥。于是她四下看了看,很快选定一拢被束起的委地锦幔,随即躲进去里面,从头到脚皆被藏得严严实实。
不多时两个婢女便将手头的活干完,出殿门时又仔细检查了检查,然后将门小心带上。
殿内各角皆摆置着铜熏笼,将偌大的屋宇烘出融融暖意,浑似身处暖春。沈姮被卷在重重锦幔中,加之身上穿的是冬裙,久了难免觉得闷热,于是打算出来透口气。
偏偏此时听见门外尚未走远的两个婢女恭敬请安的声音:“王爷。”
刚钻出来的脑袋受了惊般立马缩了回去,沈姮紧张的快速眨巴眼睫,设想过会儿李玄璟进门后她如何露面才不至太过唐突,如何开口才不至太让他为难。
以及,万一他认出自己就是上回龙泉驿藏在案下的人,又应当如何解释。
衡量再三,沈姮决定不承认为妙。
毕竟龙泉驿一事犯了太多忌讳,她牵涉其中绝非好事,倒不如干脆咬死了不认。反正长案掀翻之时李玄璟正与驿卒打斗,与她对上的那一眼不过匆匆,没理由就能笃定。
沈姮做出决定时正逢李玄璟推门而入,外头的风瞬间灌入殿内穿堂而过,拂动着帘幔起舞。偏偏有一拢幔子有些特别——仅起了点水波纹,根基却仿佛立得很稳。
李玄璟的目光短暂停留,而后走到书案后提笔挥书。
沈姮听见挪椅的动静,知李玄璟定在埋案处理公务,忖度着此刻突然出去会不会将他吓一跳?
她从不是个以吓唬人为乐的性子,是以踌躇半晌,脚始终未能迈出去。
后来宋侪进来一边回报着军中的琐事,一边伺候笔墨,李玄璟让他开了一扇窗,又抬了抬下巴指向那个有些怪异的锦幔,吩咐道:“将铜熏移到那处。”
宋侪只当是自家王爷想通气又嫌手冷,立马照做,将角落里的铜熏搬到了当央的锦幔下。
风不断从洞开的窗子灌进来,将熏笼里的火苗卷高,里头烧的虽是上好的银屑炭,无烟无味,可这热浪却是将锦幔烘烤得渐渐发了烫,裹在里头的人儿,自然也如隔水蒸煮的螃蟹,脸面一点一点的变红……
最后她终是承不住了,便也顾不得那许多,将身前锦幔猛地一掀,从里逃了出来!
狼狈周章自是不用说。
在里头闷了个够呛,出来后甫一接触到窗外送进入的清风,沈姮弓腰扶膝本能的大口吸着,待身体稍缓后恍然记起了当下所处,缓缓将身子直起来,发现对面的四只眼睛正一错不错的盯着自己。
一双很是镇定,嘴角噙着丝隐含讥刺的笑,仿佛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
另一双却瞪得大大的,很是愕然,半晌结结巴巴吐出两个字来:“女……侠?”
细细端量后,宋侪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果然没有认错,眼前的女子虽身穿王府婢女的裙衫,却分明就是龙泉驿给众人预警并将煨毒的兵器带走的那个女侠!
虽则不知她所图为何,但他深信她是友非敌,于是转惊为喜,分外热情的迎上去两步:“女侠怎会出现在王府里?可是又有什么消息要提醒我们?”
沈姮预先理好的说辞噎在喉咙里,既意外于自己又一次如此窘迫的出场,更意外于王府中人对自己的反应。
迟疑间,已是错过了最佳否认的时期。
缓了缓,她支支吾吾:“那个……我找你们王爷确实有要事相商,能不能请你……”
话未说完,就被对面一直未言的李玄璟冷声截断:“退下。”
宋侪怔了一瞬,随即应声退了出去并将门关好。沈姮目送着他,透过窗子发现他并未离开,而是正尽责的在门外守着。
敛回目光时,不期然与李玄璟冷沉的眼眸相撞,她便即屈膝为礼:“见过宸南王。”
李玄璟唇畔的那丝笑意愈显刻薄:“怎么,上次看本王沐浴未看够,这次追上门来了?”
语落之处,屋内安静至极,周遭人事俱皆凝滞了一般,唯余熏笼内火苗蹿动发出“呲呲”的细索声响。
名贵香片散出的淡淡清味在殿内环旋,将银屑碳的零星炝味覆过。这香气本可抒人心脾令人放松,可眼下沈姮却绷着身子杵在当央,两手僵僵的夹在身侧,脸面窘得抬不起来。
她以为李玄璟顶多也就看到了藏在长案下的自己,却不想他连她窥见沐浴的事都省得,她很想问一句他是何时发现的,既然发现了为何还状若无事的继续在她面前沐浴?
可一想到两回见面都是自己私闯理亏,便也没脸问出口了。
最后只以万分诚笃的语气认错:“不请自来是我的不对,但也确实事出紧急,关乎生死,故而才斗胆冒犯了王爷……还请王爷宽宥。”
李玄璟倚靠在梨花椅上,身姿放松,静静听她说完后,搭在扶手上的右手略抬了抬,指端轻叩梨木,颇有节律:“你父亲可曾告诉过你,亲王乃降天子一等之爵,若今日登门的是你父亲安信伯,想必会先本本分分的给本王行一套全礼。”
这是要自己跪拜于他?
沈姮脑中霎时间闪过这念头,旋即才又意识到李玄璟竟已识破了她的身份!
她蓦地抬起头来,目光在半空与李玄璟交汇,尽管他薄唇微弯并无不虞之相,但狭长的黑眸如鹰视狼顾般盯向她,携着咄咄逼人的威压。
这叫沈姮不自觉就有些退缩。
与李玄璟的幼时情谊是她求上门来的唯一,可眼下在他的脸上,她却连分毫忆及往昔的意思也寻不见。
八年未见,彼此容颜早已大改,他不再是那个温吞的少年,她也不再是扎着两个小辫儿吐字不清的小女娃。
且不论是在龙泉驿还是在这里,她都从未开口介绍过自己一句,然而他却已然知悉。
沈姮突然感到后背有一阵凉意掠过,恍惚间觉得在他目力所及之处,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它能轻易洞悉任何。
不过但沈姮也明白,抛开垂髫年华的情谊,依礼她的确应该向他行个大礼。
是以她提了提曳地的长裙,屈膝欲下蹲,却听见略显疏懒的几个字从上方飘过来:“这次就免了。”
她屈了一半的膝直起来,然后看着李玄璟,似在等他下一步的指示。显然这局势已是被他一人掌控。
然而李玄璟眸色陡然一转,眸底掠过的两道深湛透出两分好奇来:“你刚刚说事出紧急,还关乎生死?”
“是。”沈姮点点头。
就见李玄璟唇边的笑意慵懒漾开,戏谑的口吻问她:“关乎谁的生死啊?”
虽则已拿不准如今李玄璟的性情,但左右也无其它出路,沈姮觉得既然已经来了且挑开话头,不妨合盘托出试一试。于是鼓了鼓气,将皇上突然下了一道圣旨封她为公主,准备送她去南诏国和亲的事详细道来。
末了,又补了句:“王爷初初回京,想必尚不知晓这些,但我听父亲说曾劝服过皇上收回旨意的人,满朝只有您一人。所以冒死前来求见王爷,希望王爷能念在儿时情谊上——”
“儿时情谊啊?”
还不待沈姮将话说完,李玄璟就出声截断,神情也颇是微妙:“难道没人告诉你,和亲的奏疏是谁所呈么?”
沈姮微微怔然,此前她倒是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只当圣上突发奇想。现下被李玄璟提醒,显然他意有所指,她心中隐隐有了个不祥的预感,半晌才颤颤问:“是……谁?”
那双眼睛一改之前的冷厉,忽地融了笑,似看到了什么有趣的西洋景儿。
从这双渊泽般的眼睛里,沈姮仿佛看到一个答案呼之欲出,可他偏不肯直言相告,就这么吊足胃口的看着她,直看得她再次退缩,将头低下。
就在她长睫垂落掩住眸光的那刻,他溢出一声几不可闻的轻笑:“是本王。”
饶是刚刚透过李玄璟的神色,她已有了这种猜测,可听他亲口说出来,她还是心头剧烈的一颤。明明那熏笼就在身后,将她整个后背烤得炙烫,可一股冷寒却游蛇似的爬过她的脊梁骨,寒得令人发怵。
“为……为什么?”
天底下不会有比这再好笑的笑话了,她视为救命稻草的昔日玩伴,竟是亲手将她推入火坑之人。可她想不通,即便他不念旧时情谊,又何故将事做得如此绝?
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支撑着此刻重重打击下已脆弱不堪的她抬起了头来,咬着下唇,眼中血丝浅布。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她的声音比先前要高了几分,似在诘问。
李玄璟微微蹙起的眉头表达了他对眼前小姑娘态度急转的惊讶,先前还是一副眸光瑟缩,话也说不利索的小模样,转眼就秀眸猩红,口齿狠厉。
她以下犯上,他倒也不恼,沉着又合情理的回答:“自然是为了大周。”
这冠冕堂皇的说辞沈姮自是不会相信,追问:“那为何偏要选上我?”
李玄璟从梨花椅中起身,双手负在身后缓步朝她踱来,皂靴踩在云纹朱锦提花栽绒毯上,行走间悄无声息。
“年初礼部侍郎府上的郎君起了诗社,大办春日宴,听闻当时长安的贵女才子去了半数。佳人赏花扑蝶,才子们题诗作画一派热闹,留下不少佳作。其中一幅月下仙子浣发图流传最广,令沈氏女名躁一时,一跃成为京中贵女的翘楚,引得无数才子竞相折腰。”
说话间,李玄璟已自右走到了沈姮身侧,微歪着脑袋度量她。
咫尺之距,沈姮被他看得脸颊滚烫,加之想起那时的画面,更觉得羞臊难当。
那时宁云笙起了诗社,一心扬名,为了不输与同窗的比试,央她坐在池畔散发入画。
虽说后院除了她和宁云笙并无旁人在,浇水浣发之景也是他临时起意在画中虚构的,但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理应注重仪容,于人前披头散发,委实不成体统。何况那姿态还入了画作,被人肆意传阅,竟连远在宸南的李玄璟都能听说。
那大抵是她这辈子做过最荒唐的举动了。
这样近距离的看着小姑娘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李玄璟莫名觉得心里畅快,信手一挑,将她发间一缕青丝绕在了指上。登时淡淡兰香沁入鼻息,就同儿时的感觉一样。
他知她自幼喜爱兰花,所用的香膏熏料皆会混入兰香,那时他教她骑马,她骑在木马上他俯下身子来教她握缰绳的姿势,下巴就抵在她的头顶,总能嗅到这味道。
许多年了,这味道都不曾淡出过他的脑海。
沈姮挑着眉眼看他,清冽的眸子里已有了明显的羞恼之意,只是羞恼之外是万分不解,她不解他为何对自己有这样大的敌意,轻浮,傲慢,甚至还想要她去死。
她水眸猩红的望着他,却似个布偶一样由他摆布。
“世人皆道兰花素洁脱俗,却鲜少人知它还有个俗名,叫作媚世。”
李玄璟轻佻的眸光落在沈姮樱珠似的唇瓣上:“就是不知咱们盟国那位钟鸣漏尽的老皇帝,可会喜欢?”
纵是沈姮一直敬畏着他的亲王身份,可在如此轻佻的动作言语下,她也难再拘着上下尊卑理念。她蓦地抬手重重甩在李玄璟的手腕上,意图将他正撩拨在自己发间的那只手拍开。
她却忘了他在疆场厮杀多年,已然是一名出色的武将。
那散发着玉曜光泽的肌肤下,也同样有着玉石一样的坚硬度,她的手背挥在他腕上的瞬间,非但未能将他的手推开,反倒令自己纤细的腕子折了一般,赶忙捂住!
疼得忍不住发出一声痛嘶。
李玄璟垂目扫了一眼她红肿的手背,闪过一丝无奈,终于肯饶过她似的将手敛回负到身后,脚下也挪开了半步。
一改先前浮滑放荡之态,义正言辞的道:“为缔两国盟约,南诏皇帝以后位作聘求娶我朝公主,我朝也理应擢选出最具美名的贵女封为和亲公主。如此方能体现我泱泱大国子民的雍容之态和瑰丽之资。”
他的话义正言辞,仿佛所作所为皆是以家国大业为出发,叫人挑不出错来。
沈姮已顾不得手背上的疼痛,只觉心底似破了一个大洞,有冰一样的冷泉股股往处冒,将她的一身热血浇熄,浑身如浸冰窟。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改变自己命运将自己推去火坑的,竟是当初宁云笙好胜心下的一幅戏作!
未婚夫君令她名扬长安内外,昔日旧交又将她举荐给皇帝,可怜她还曾想过求助于他们……
“我知道了,谢王爷如实相告,告辞。”
利落的行了个告退礼,沈姮转身出了殿门。
事到如今她才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叔父们放弃,祖母放弃,父亲放弃……都不打紧。
只要她自己还在努力着,一切就还有转圜的机会。
门外戍守的宋侪原本站出来想拦,看了眼李玄璟的眼色,立马将路让开,由着沈姮面无表情的离开。
待她走远了,宋侪才问:“王爷,就这么让她走了?”
李玄璟负手立在当门,目视着那个纤弱又僵硬的身影刚刚消失的转角,淡淡道:“很快还会见面。”
他这话说的不假,就在万寿节前两日,宫里的中官又来了一趟安信伯府,叫沈姮准备准备,明日随他进宫面圣。
虽说沈家人已有了心理准备,却没想到进展得如此之快,原以为至少要过了万寿节才会有动静。如今消息一来,府里众人各怀心思,也开始了各自的动作。
老太君在众人面前时沉默不语,回到自己院里便取了钥匙,吩咐贴身的嬷嬷去库房里将她当年陪嫁的一套红玉缠枝石榴花头面取来。
这套头面是当年诸多陪嫁饰品里最贵重也最好看的,然她年轻时也是个沉稳性子,艳物都看不到眼里去,才一入府便让人仔细收起,再未取出来过。
此时拿出来自然是想给沈姮添了嫁妆。
原本老太君早早给几个孙女备下了差不多的嫁妆,可眼下沈姮的出路是要比旁人都高的,自然紧着好的添去她那。
虽说是千里迢迢嫁去南诏国,可到底是去做皇后。这是祖辈积下来的福报,竟叫他们沈家出了一位皇后!
收到这副头面的沈姮,坐在铜镜前看着镜中自己素洁的容颜发呆。翠影站在一旁丧白着脸,不知事到如今还能劝些什么。
苏嬷嬷走到妆镜旁,握过沈姮的手,轻轻在她手中划拉几下。沈姮和翠影都看出了,那是一个“逃”字。
“对,姑娘您快趁还没进宫面圣赶紧逃吧!圣上至今还没明确提及和亲之事,您现在逃了便不能算抗旨逃婚!”翠影连忙附和,焦急的恨不得当下拽着自家姑娘远走高飞。
沈姮推开她的手,“嬷嬷说的是,逃是当下唯一的法子了,不过不是现在。”
“那要等何时?”
施施然移步窗前,沈姮望向南方,目力似穿越层层墙垣:“等我被送亲的队伍送离长安,送离大周的边境……”
“那岂不是到了南诏?”
沈姮笃定的点点头:“如此才能不连累沈家为我一人的生而陪葬。”
打从中官传达了消息离开后,安信伯便独自进了书房,房门紧闭,一闭便是整整一日。
若他猜得不错,明日圣上招沈姮进宫,除了想亲眼看一看自己钦封的这个和亲公主外,应当还会安排南诏的使臣与她见上一面。
前几日他为此事四处奔走之时,便曾听闻南诏国的使臣对于圣上封和亲公主一事稍有微词,比起沈姮这个贵女提封的公主来,他们似乎更喜欢另一位长乐公主。
虽说长乐公主行事作风颇为豪放,公主府内养着面首男宠无数,甚至不久前还将一位隽秀的小和尚强纳回府,但到底是货真价实的大周皇室血脉,不是一个小小伯爷之女能比的。
想通此节后,沈之槐突然心生一计,趁着夜色未深去了一趟兰月苑,对女儿私下交待了几句。
他走后,翠影和苏嬷嬷进屋发现沈姮的神色果然放松了许多,翠影便急着问:“姑娘,伯爷可是想到什么法子了?”
沈姮淡然的笑笑:“或许除了逃,还有一计可以试上一试。”
明日沈姮面圣的事不仅牵动着老太君和安信伯的心,西院的母女二人亦是为此早歇不下。
沈素坐在床畔泪眼婆娑,一脸的焦灼,若被不知情的人见了必定觉得她与沈姮姐妹情深,难舍难离。
只是一开口,难免泄了真实心思:“阿娘,四妹妹明日进宫面圣,该不会真向皇上说要我作随嫁的媵女吧?我死也不去南诏!”
“她敢!”秦氏愤然将手中茶盏往桌上用力一镇!
这动静将本就心思脆弱的沈素吓得更是一抖,秦氏连忙走过去心疼的抚了抚她的背,安慰道:“那死丫头就是看你老实唬你罢了,到了圣上面前哪还有她说话的份儿?”
“真的吗阿娘?”
“自然是真的!”
纵是有亲娘陪在身边温柔抚慰,这一晚沈素依旧梦魇不断。
梦里她跟着送嫁的车队行在无垠的荒漠里,没有水,只有炎炎酷日,将她嘴唇暴晒得干涸泛白。
前方的路望不到头,她走了一日又一夜都没能走出去,直到清晨的天光透进帐子里将她照醒,眼角犹泪痕未干。
若说偌大个安信伯府里有没有谁睡得安稳香甜?那还真有两位。
一位是二房的老爷。
他人在刑部混了十几年,却还只是个六品的比部司员外郎,在长安这种五品都只能算芝麻绿豆的地方,委实日子过得有些憋屈。
如今亲侄女成了公主,他也算沾着皇亲了,往后再有空缺肥差时,就不信尚书大人和侍郎大人能不顾念这层关系!
另一位则是三房老爷。
打从成亲后他便跟随岳丈经商,在外人眼里难免有受妻族恩惠吃软饭之嫌,就连内侍监那些断了根的家伙也常拿这件事来打趣他。
这回他沈家突然出了个为保家国平安而和亲远嫁的巾帼英雄,这实在令人敬仰。
有这样了不起的侄女在,日后不论在岳丈一家面前,还是在内侍监那些阉人面前,他的腰杆儿都能跟着硬起来!
这一夜,众人心思复杂,沈姮也没怎么睡。倒并非她心思沉重睡不下,而是有意磋磨自己。
待得翌日天亮上妆时,她的眼底已如愿熬出了两团乌青来,眼中也密布起了血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