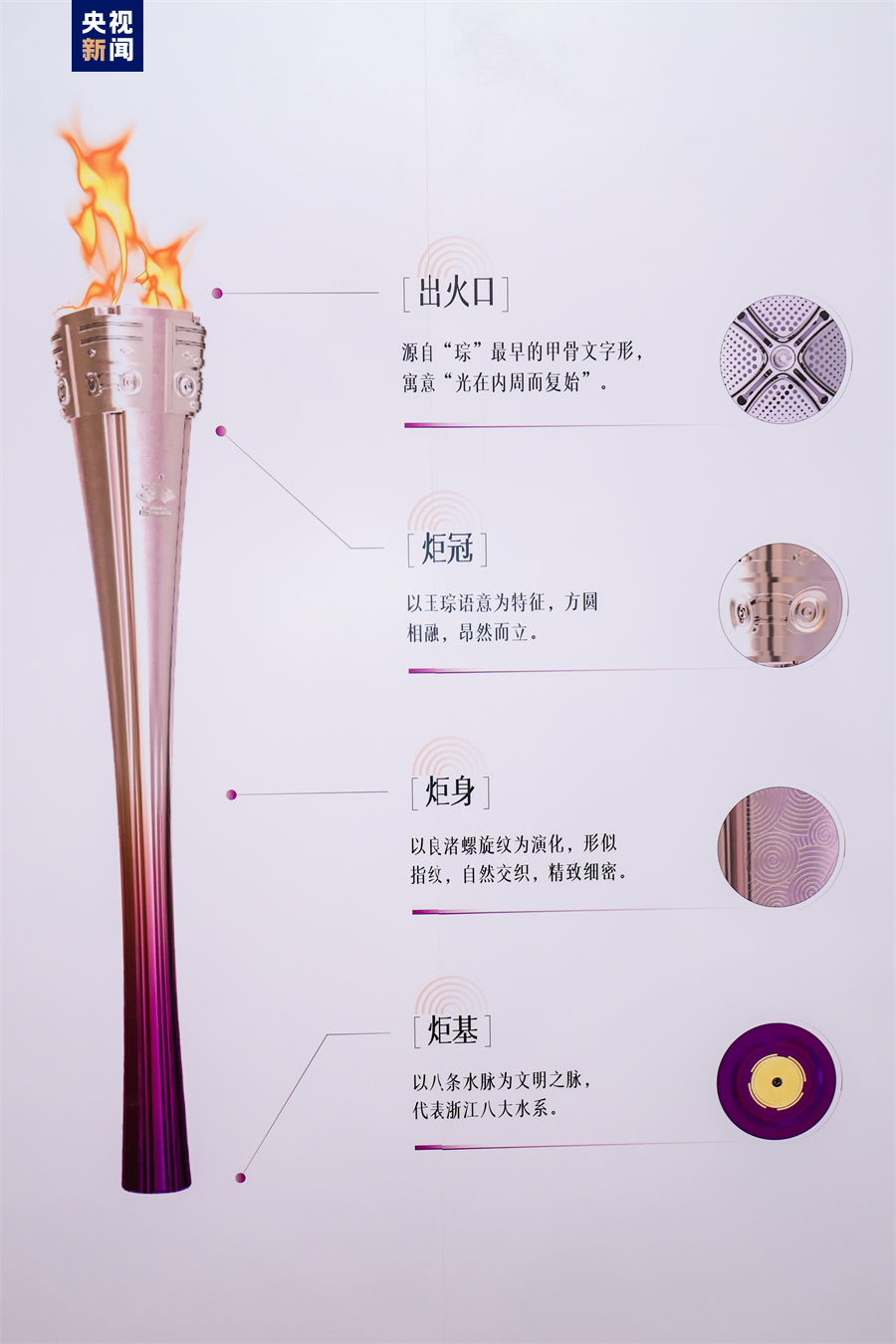当年万里觅封侯汤铭目的_当年万里觅封侯汤铭是谁
任凭风霜摧残,
八千里刀山火海蹚过,
即使让这坎坷命运磋磨得面目全非,
少年心中自有絜矩。
————————————

哈喽,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漫漫何其多的《当年万里觅封侯》,是一本很搞笑的作品。
漫漫何其多非常擅长用搞笑的口吻讲述一些悲伤的事情,这本书里,最让人唏嘘的大概是少年人之间的错过,和归来后一如往昔的情谊。全文搞笑轻松,故事线也清楚明了,伏笔有几处,但不是很难猜,难猜的是故事人物的内心。
喜欢轻松一点的文的宝子们可以冲了,这本书入手不亏~
故事简介:
钟宛,字归远,曾是鲜衣怒马少年郎,足智多谋,连中三元。
在夺嫡失败后受委托带着自家小主远离京城,为了保命护主,不断在外散播自己与年少同伴郁赦的风流谣言。
郁赦,字子宥,他本是风度翩翩贵公子,少年温润似玉天上月。
他与钟宛自小相识,两生情愫,但却受旁人阴谋诡计驱使,不仅与钟宛生离,还变得阴暗疯癫,喜怒无常,典型一个病骄世子。
当风流情史传到正主耳朵里,不仅没有气疯,还受流言日日熏陶,深受其害,一心认为自己和钟宛就该那样,助长了流言的传播。
好在七年后他们重归于好,但也因那些风流情史闹出来不少笑话,浪里小白龙钟宛让郁赦心中掀起阵阵波澜。
"钟少爷说太医给他诊出了喜脉,让世子无论如何回去看看。"
郁小王爷说:"再多药材也只医得了他的身子,你医不了他时时刻刻要粘着我的心。"
但最意难平的仍旧是他们分开的那七年,就像郁赦说的,"钟宛他本也是世家公子,我同归远,原本是门当户对的。"
"我们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
名场面集锦:
郁赦静在一边,神色自然地听着钟宛念话本。
民间话本,写得再好在两人面前也略显粗糙,有不通不顺之处,钟宛念的时候当场就给改了。只是没想到郁小王爷过目不忘,早已逐字逐句熟记在心,故而每次听到他的校对,嘴角都微微勾起。
相较而言,钟宛简直如坐针毡。
前面就算了,读到后面,钟宛仗着自己才情过人,略了好些句子,再将前后润色一番,妄想瞒天过海。
可惜骗不过郁赦。
郁赦品着茶,打断他:"你少读了一句······翻回去,重读。"
钟宛:"······"
"他再也撑不住,他······"钟宛闭上眼静了静心,睁开眼继续念道,"他······他······"
郁赦好整以暇地看着钟宛,眼底带着几分戏谑。
钟宛终于绷不住了,将书摔到桌上:"他不想读了!"
郁赦撑不住,闷声笑了起来。
钟宛耳朵微微红了,偏过头看向窗外,磨牙:"你以前······明明什么都不懂······"
"后来我就全懂了。"郁赦笑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把话本拿起来,抚平封皮上被钟宛摔出的折痕,"好看吗?"
钟宛咬牙:"好、看。
郁赦笑了:"那回头我再给你送些。"
钟宛声音发颤:"你······还有许多?
郁赦点头:"自然,郁王府书斋里,有十来个书柜里都是此类话本,比这本好看的有很多。"
————————————
第二天,天一亮,钟宛就开始作死。
"郁赦,你天天这么跟我在一起,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
少年郁赦近日在给前朝的一套古籍做批注,一心两用,闻言古井不波道:"什么?"
自打那天把钟宛熏倒,让他睡了一个安稳觉,少年郁赦就觉得钟宛不应再提防自己了。
钟宛安静了一会,问道:"郁赦······你知道吗?男人的好年纪,其实就这么几年。"
年过半百,伺候在一旁的冯管家:"······"
郁赦抬头,甚至觉得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我说我自己啊。"钟宛坦然道,"时光如白驹过隙,等过两年我是什么行情就说不好了。"
郁赦压着火,低头继续批注,不理会他。
钟宛静了片刻,又小声道:"郁赦,你知道吗?没有什么是会在原地一成不变的。"
郁赦:"······"很好,这是越聊越深了。
郁赦深呼吸了下,依旧装没听见,沾了沾墨。
钟宛开始反间了,指了指冯管家:"你看不上我,别人就不一定了。"
冯管家大怒:"你说什么?!我我······"
冯管家百口莫辩,急急忙忙地向郁赦表忠心,"我看管钟少爷的这三个月里,没多看过他一眼!天地可鉴!再说,再说······老奴都五十四岁了!我就是有什么心思,我能做什么?!"
""欸!钟宛劝慰冯管家,"我不许您这么说自己!"
冯管家登时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郁赦无奈地放下笔,叫来仆役把冯管家扶下去了。
————————————
郁赦欲言又止,重新拿起书来了。
钟宛眯着眼,突然觉出哪里不太对了:"郁赦······你是不是并不喜欢这们亲事?"
郁赦沉默片刻,道:"母亲给我选的,我自然喜欢。
"我不觉得。"钟宛上下看看郁赦,"你要是真喜欢,我刚才一问你就该说了,就算你不爱聊天,也会忍不住多提两句的,真的倾慕谁······是藏不住的。"
郁赦手里的毛笔一顿,一个小墨点滴在了书上,缓缓地晕开了。
真的倾慕谁,藏是藏不住的。
————————————
"等等。"钟宛突然道,"还有件要紧事,我要问你。"
林思认真地看着钟宛。
钟宛沉声道:"前些天,郁小王爷是不是抓了你去,问我小名?"
林思愤愤不平,比画:郁小王爷蛮横又不讲道理!他问主人你的小名,我当即就要说!奈何他上来让人按住我,我一个哑巴,口不能言,白白吃了好半天苦头。
钟宛回想自己厉声质问郁赦是否刑讯林思的场景,满目苍凉。
钟宛无力地摆摆手:"委屈死你了······你去吧。"
林思耿直地磕了个头,走了。
————————————
第二天清晨,钟宛坐在床上,目光空洞地看着床尾自己的外衫。
钟宛记得清清楚楚,昨晚他绝对没脱这件衣裳。那是······怎么被脱下来的呢?衣裳还被折了两下,显然不会是梦中不适自己脱的。
外面冯管家敲了敲门,推门进来,偷瞄了一眼钟宛。
钟宛问道:"昨晚······郁小王爷回府了吗?"
冯管家谨慎点头:"一回来,就来您这里了。"
钟宛绝望了。钟宛疯狂回忆,自己昨晚有没有嘴不严,说了不该说的话。
冯管家小心问道:"钟少年,你要不要、那什么,要不要······"
钟宛声音发抖:"不要热水!"
冯管家咽了下口水:"好,好,不要,但您······您这么安静,我倒不放心了。"
"那好如何?"钟宛万念俱灰,道,"我现在应该哭哭啼啼吗?"
————————————
钟宛深吸了一口气,下了决心。
郁赦失了耐心:"钟宛,没人教过你要在事前把要求说明白吗?有什么要求,一字一句,现在,说清楚。"
钟宛抬眸看着郁赦,声音很轻:"是······有件事要求你。"
郁赦低头,几缕额发垂了下来,让人看不清他的神色。
郁赦自嘲一笑:"果然。"
郁赦冷冷道:"就一件事?"
钟宛点头。
郁赦倏然抬眸,喝道:"说!"
"你······轻点。"
————————————
钟宛看着被退回来的食盒,久久 无言。
自己殚精竭虑,日日替郁赦忧心,但郁赦整日都在做什么?!
先不说这个,郁赦将来要是娶郁小王妃,也会这样和自己的王妃约法三章吗?
大婚之夜,脸色阴沉地给自己的王妃定规矩:每隔十日,你可以来我床上躺一躺,其余的,你休要多想!
成婚十年后,郁王妃若是表现好,郁赦或许会格外开恩:以后每隔七日,你可以见我一面。
成婚满二十年,郁王妃或许就有那个荣幸可以牵一下郁赦的手了。
成婚满三十年,郁赦终于能接受彼此亲一下了。
钟宛以前只是听说过有人于情事上有些慢热,但万万没想到,还有慢成郁赦这样的!
按这个进度算,若三十年才只能亲一次,那······那······
那种事呢?!郁赦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在垂垂暮年时,郁王妃披荆斩棘,通过了郁赦几十年的层层考验,闯过了九九八十一关,终于取得了郁赦的信任,可以同他······
这真是用尽自己一生,去考验一个人了。
钟宛万念俱灰,对郁赦来说,也许那顶顶亲密的事,是一生只能做一次的?
一生一世,只做一次。钟宛神情恍惚地打开食盒,咬了一口点心,喃喃:"郁小王爷对他自己的头一次,可真是太看重了······"
————————————
子宥温柔如斯,一如往日。
钟宛抬眸,看着眼前神情冷漠的郁赦,轻声道:"世子,你明明没那么恨我,包个伤口也要这样小心,何必每日对我喊打喊杀地吓唬人?"
郁赦一怔,瞬间有些失神,似乎在压抑着什么,片刻后胡乱呢喃道:"我待你凶狠些,对你我都好······"
钟宛恍惚,皱眉:"什么?"
郁赦喃喃低语:"我待你不好······来日我死了,你也只会觉得快意,不会伤怀。"
钟宛眸子一颤。
郁赦这会儿半疯不疯,一不留神,让钟宛隔着千万重山水,瞥见了他的一点年少时的性情。
钟宛心中怆然,忍不住轻轻拍了拍郁赦的脸。
————————————
郁赦默默地看着书案上的字,道:"我觉得,我待他很不好。"
冯管家心道:您才知道吗?郁赦闭上眼,忍不住怒道:"但我没想到他有那些毛病!不罚他又不行。"
冯管家好奇死了:"什么毛病?"
郁赦沉默了片刻,也想找个人说说,不堪重负地摆摆手:"先把门窗关了。"
冯管家如临大敌,方才争储的事都能敞开了说,现在倒要紧闭门窗了,这是什么关乎性命的大事?!
冯管家去料理好了门窗,折回来屏息听着。
郁赦嘴唇动了动:"他有些不好的癖好。"
冯管家声音比郁赦还轻:"什么癖好?"
郁赦低声道:"昨天半夜,他不知从何处找来了绳子,放在床上,入夜后拿着绳子哼哼唧唧的······想让我绑着他。"
冯管家:"······"
冯管家小心翼翼地提醒道:"世子,旁的先不说,那绳子,不是您让我寻过来的吗?"
郁赦看怪物似的看向冯管家,满眼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让你找过绳子?!"
冯管家倒吸了一口凉气。
冯管家在心里替钟宛扼腕,钟宛这命是真的不好,每逢要紧事,就赶上郁赦犯病,这桩移花接木实在是冤。
郁赦失神道:"他这些年到底是怎么了?还是自小就喜欢如此,只是我少时太蠢,没发觉?"
冯管家硬着头皮道:"可能是一直就这样吧。"
冯管家怜悯地看着郁赦,不忍心告诉他,他这其实是犯了一天一夜的病,到现在还没清醒。
冯管家想了想,如履薄冰地吃力劝道:"世子估计昨晚没休息好,要不现在眯一会儿?"
郁赦不知听没听见,磨牙:"他真是······不知死活。"
冯管家点头如捣蒜:"是,是,钟少爷不知死活。"
"但是!"郁赦意难平,"我是不知道他偏爱这个调调!将来我躺在地下,若亡灵有感,知道他被姘头夜夜困在床头折磨,我怕是被气炸尸,掀了棺材板!"
冯管家目瞪口呆地看着郁赦,已然跟不上郁赦的思绪了。
这怎么还······说起鬼鬼神神的事了?
冯管家一砸手心,大声道:"所以世子不能死!"
"是。"郁赦揉揉抽疼的额角,"我先去睡一会儿······"
冯管家亲自把郁赦送进卧房,伺候他躺下后,健步如飞地回到自己院里,提笔给钟宛写了封信。
————————————
钟宛千算万算没料到,时隔多年,被他坑了的郁赦,在今日将这些事默默地替他扛了下来。
郁赦神情自然,嗤笑:"你准备如何?跟小时候似的,宣瑞背不下来书,你替他挨手板?"郁赦拿起书案上的礼单,呢喃,"那这次可不是一顿手板就能了事的······"
郁赦把书案上的"证物"都看了一遍后抬头,见钟宛神色有异,脸上的笑意渐渐淡去。
郁赦审视着钟宛,眼睛微微眯起:"我懂了,从始至终,你就没想到我会帮你。"
钟宛担心郁赦误会,声音艰涩:"不是,原本就是我的错,我不能让你······"
"钟宛,"郁赦打断钟宛,眼神平静地看着他,有些突兀地问道,"许多年没人待你好过了吧?"
钟宛一时没明白郁赦东一句、西一句地在说什么,下意识要反驳,但张了张口,居然没说出什么来。
郁赦看向钟宛,平静道:"不然,怎么我就简单帮了你这么一把······你就如此惶惶不安呢?"
钟宛语塞。
自去了黔安,所有事就全落在了钟宛肩上,没人能商量,也没人能倚仗,钟宛早就习惯了无论出什么事自己先顶上。
"这些年,"郁赦把手里的信函和礼单一并丢进炭盆里,火苗噗地冲了上来,轻嘲,"我过得不顺,你也不太容易吧?"郁赦拨了拨炭火,"你要是不习惯,不明白,看不懂,察觉不出来,察觉出来了也觉得其中还有别的什么······那我就说得明白点。"郁赦看向钟宛,"我这是在为你痛心。"
————————————
郁赦起身,拿起床头佩剑,刚走到窗前,突然听到外面呜咽几声,好似······什么野兽的叫声。
郁赦迟疑间,外面那野兽突然似半人半兽的高声鸣叫——
"钟宛不能走!钟宛不能走!钟!宛!不!能!走!!!"
郁赦:"······"
郁赦拿着佩剑的手微微发抖,本能地怀疑自己——自己这是······彻底疯了吗?
郁赦难以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犹豫着退回了床上。
转过天来,被那不知是什么的野兽嚎了一晚上的郁赦眼底发青地坐在桌前,又在自我怀疑,没有清醒。
冯管家蹑手蹑脚地走到桌前,小声道:"世子没睡好?"
郁赦愣了下,下意识道:"茶······"
冯管家巴不得听这一声,忙端了茶盏来,颤巍巍地,没拿稳,倒在桌上,杯倒茶流······
冯管家骇然地指着桌子:世子!你看!!!
郁赦转头看向桌子,只见那茶水泼了一桌,但偏偏有灵似的,避开了道道笔画,隐隐显现了几个字:钟宛不能走。
郁赦表情僵硬,半晌说不出话来。
郁赦闭了闭眼,尽力不去想到底是自己疯了还是这世道疯了,一头钻进了书房里。
晌午,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郁赦舒了一口气,刚要起身,外面冯管家攥着一条滴血的死鱼,满脸震惊地冲进了书房。
郁赦:"······又怎么了?"
冯管家惊骇地拿着那条死鱼,结巴道:"世子!厨下方才在宰鱼,想着中午给钟少爷炖鱼汤,没想到啊没想到!一刀子下去,在鱼肚子里发现了这个!"
冯管家从鱼腹中掏出一张还未湿透的字条。满脸敬畏地递给郁赦。
郁赦麻木地接过,将字条打开······
字条上写着五个字:钟宛不能走。
郁赦:"······"
冯管家满目:"这是天象啊······"
郁赦五指一攥,将这沾着鱼腥的字条揉成一团,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去······告诉钟宛······我不会赶他走了······还有······"
冯管家大喜,不等他转身,郁赦又拿了一本《史记》出来,丢给冯管家,崩溃道:"让他把《陈涉世家》抄十遍,连着上次的《心经》一起给我!"
————————————
狐鸣篝火,鱼腹藏书。
身为同窗,都是在是老太傅手下读过十年书的人,郁赦还比钟宛多读了几年,谁比谁傻?郁赦就算课业上比钟宛差了些,也不至于连《史记》都没背过。
而且——郁赦将手心的那张皱巴巴的字条展开——故弄玄虚地用篆体写这几个字罢了,这显然是钟宛写后冯管家誊抄的,照着葫芦画瓢,还描错了两道笔画!
若真是天相,还能有白字的?!
郁赦被钟宛气得耳鸣,昨晚他一夜没睡,整夜都在忧虑自己病情有加重了,设想了许多情况,连托孤的事都考虑到,万万没料到······郁赦晕头转向地去补眠,另一边,冯管家赶着去跟钟宛报信,先欣喜大事已成,又忍不住嗔怪钟宛:"我就说只在桌上涂点儿蜡就行了,你非要弄那死鱼,血淋淋的······吓得世子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你之前还说万无一失,还说你若是个女子入宫为妃必然斗得其他妃嫔裤子都穿不起,你······你这也没多厉害。"
————————————
"吃了?"郁赦书案上摞着高高的两沓公文,头也不抬,"有效吗?"
太医低声道:"钟少爷这些天每日按时吃药,只是要有效······怕是现下不能,药丸里大多是补药,且药性温和,须得天长地久地吃下去才能看出些成效来。"
郁赦点头:"他没起疑心吧?"
太医顿了下,低声道:"钟少爷方才问我,这是不是保胎药。"
郁赦手中的笔一滑,在文书上画出一道墨迹来。
太医困惑地看了郁赦一眼,想着外界传的与郁小王爷性情古怪的事,慎重道:"世子,恕我直言,男子是不能······"
"别说了。"郁赦把文书丢在一边,重新拿了个空白的来,摆摆手,"去吧。"
太医小心翼翼地溜了。
————————————
隔间,钟宛手指发抖,几番忍耐,最终哭忍不住,"哇"地喷出了一口血。
郁赦脸色骤变,嘶声道:归远!!!
电光火石之间,隔间外的汤铭、宣瑞大惊,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外面林思破门而入,家将们跟上冲了进来,家将身后还有一个被郁赦暗中吩咐带来的宣瑜和宣从心。
宣瑜小脸苍白,被人推搡着上前,怔怔地看着宣瑞。
宣瑞被这阵仗吓坏了,好半天没反应过来,呆滞片刻,哑声道:"你俩······怎么来了?"
宣瑜抖着嗓子:"哥······你刚说的,是什么啊?"
宣瑞只见林思时,还没多害怕,闹不清这些人是不是自己府上来救自己的,只白着脸失神道:"你不懂,我回头同你说,你们怎么来了?这些人是你们带来的?"
宣瑜难以置信地看着宣瑞,还在问:"你刚说······钟宛是来害我们的?"
宣瑞怒道:"我没这么说!我只是······是人就有私心,你还小不懂,我回头同你说!"
"我是不懂······"宣瑜声音暗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父王是怎么死的,但······钟宛是为了我们,才回黔安的,这不是真的吗?"
宣瑞心虚地看了林思一眼,他知道林思是钟宛的心腹,怕林思回头跟钟宛说什么,情急之下推搡了宣瑜一把,低声道:"回头再说!"
宣瑜被推倒在地上,浑身发抖,踉跄着爬了起来,低声念叨:"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但······但这些年,把我带大的是钟宛······叫我识字的是他,让我明事理是他,手把手······"
宣瑜眼泪直流,仍在嗫嚅:"手把手地教我写仁义礼智信的人是他······"
宣从心双目噙泪,忍无可忍,上前一把攥住宣瑞的衣领,盛怒道:"宣瑞!!!他当年才十六岁!比现在的你还小一岁!七年来他几次差点把命丢在南疆!图了个什么?多少年来生死挣扎,就图让你这么猜忌的吗?!"
————————————
郁赦将钟宛轻轻放在地上,慢慢地走了出来。
郁赦脸色青白,眼中通红,如厉鬼一般直直地看着宣瑞,声音嘶哑:"他身上的毒······"
宣瑞一见郁赦登时吓得跪在了地上,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到底怎么了,惊恐道:郁、郁赦?"
"我······"郁赦难以置信地看着宣瑞,咬牙切齿地喃喃,"我当年是疯了?我居然故意放他走,让他去找你,我······"
郁赦口中泛起一股腥甜,他恨不得一头扎回七年前,一耳光扇醒自己。
自己是多蠢,将那么好的归远,拱手让给了这个东西。
————————————
钟宛出了一会儿神,披上外袍,慢慢地下了床,走到了书案前。
钟宛拿起笔,他有点畏冷,瑟缩了下,胸腔里火烧火燎地疼。
数年前,在狱中得知宁王身殒时,钟宛也曾喷了一口血,但那会儿年轻,没吃药没歇着,竟就那么生生地挺过去了,现在想想也没觉得多难受,这次却不行了,钟宛觉得自己肚子里好像被人埋了十多柄刀进去一般,只要稍稍一动,就扎得他五脏六腑跟着一起疼。
伏在书案上休息了一会儿,展开一张纸,提笔刚写了个"男"字,钟宛失笑,揉了丢到一边,
"宛跪禀。""宣瑞之事,料父亲······"
钟宛握拳,低头深吸了一口气,一把将纸又揉了,丢到一边,
钟宛缓了好一会儿,重新提笔。
"宛跪禀。"
宣瑞之事,料王爷、王妃在天有灵,已具悉。"
钟宛眼眶红了,咬牙忍着。
"宛自京中至封地,蹉跎数年,为求自保,无所不为,种种下作之事,料王爷、王妃亦具悉。"
"数年来,于王府,辱门败户。"
"七载间,于子宥,深恩负尽······"
————————————
"你······"
钟宛愣了下,抬头,郁赦不知何时回来了,正站在他身后。
郁赦怔怔地看着钟宛给宁王、宁王妃写的信,低声念:七载间,于子宥,深恩负尽······"
"深恩负尽,深恩负尽·····"郁赦重复呢喃,心里难受得无以名状,他闭了闭眼,握笔将这一句划了,哑声道,"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
钟宛突然不太敢看郁赦,他胸口生疼,就势低下头,沉声道:"你也听宣瑞说了吧?当年······我差点给你下毒的事。"
郁赦默不作声。
钟宛低声道:"只差一点,我就要了你的命,你不怪我?
"宣瑞觉得我是为了你,才没替宁王报仇,你怎么看?你该比他明白吧?该清楚,我其实是为了保下黔安的人才没有对你动手,一念之差,没准我当年······"
钟宛看着自己的手,低声道:"来日若再来一个汤铭,同你说,我 其实······"
"闭嘴。"郁赦打断钟宛,淡淡道,"不管你是为了谁,随你如何说,随别人如何说,在我心里······你就是为了你我的情谊,才没下毒。"
钟宛心中一震,费力道:"你······"
"我不是宣瑞,没人能蛊惑我,你也不行。"郁赦漠然道,"以你我的交情······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信。"
说好了绝不会流泪的钟宛,吃力地睁大眼,声调变了:"你怎么知道······"
"当日······"郁赦喉咙哽了下,"你走了,把我给你的卖身契、银票、路引都夹在了一本书里,那本书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钟宛咬紧牙关。
郁赦道:"是《诗经》。"
郁赦道:"是郑风。"
郁赦道:"是······子衿。"
郁赦几乎是怨恨地看着钟宛:"你当日知道留不下来,所以不肯同我说,不肯告诉我······"
"但偏偏,又留了一句未尽之言给我,青······"郁赦死死地盯着钟宛,眼睛通红,"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纵······"
钟宛终于崩溃,眼泪蜿蜒而下,哽咽道:"······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